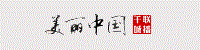3个多小时的采访,我们喝光一壶茶,美式咖啡的冰块慢慢化完,桌子上逐渐摆满来自樱园主人熊燕的款待:一碟削皮去核切好的雪梨,配了两只水果叉,一盘蛋黄酥、一碗葡萄干,用心形小竹筐装来白味花生,又拿来小簸箕装花生壳。

在屋顶上的樱园采访时,来自樱园主人熊燕的“投喂”
之所以约在樱园,不仅因为何大草自前年起在这里开设写作班,更因为这个空间对于作家的新书《春山》的出版来说至关重要。这本首印8000册,上市十天加印10000册,小说新书榜第四,这两天正位列豆瓣网“最受关注图书”榜单前五的小说,绝对可以说是畅销书。
但一开始,在熊燕将其推荐给出版社时,何大草却悲观地认为“出版社会亏本”,“我就想自己花点钱把它印出来,印个100本,然后就按编号送朋友。我想有100个人读可能都困难,我就慢慢送,好朋友他不喜欢读,我也不送他;就送给喜欢的人,可能5年都送不完,但也不重要”。
聊到此处,一旁的熊燕终于忍不住过来补充了一句:“我就觉得它是一本每个读书人的书柜头都应该放的书,就很有那种感觉。”

何大草在樱园,图源/熊燕
在3个多小时里,何大草用成都话,与我们聊了许多关于《春山》的问题:它的人物、它的语言、它的作为历史小说的虚构性,和读者对这种虚构性的理解。我们也聊起他在四川师范大学和樱园开设的写作课,他50岁左右去一个儿童班学画画的经历,他最近的主要写作项目……
更重要的是,今年58岁、写作26年的作家何大草,极为诚恳地向我们坦白了自己近年来在写作上的转向;他当下对于小说、对于小说语言最大的自觉与追求;他审慎地判断自己正处在写作生涯的什么阶段,以及,在这个阶段里,《春山》究竟意味着什么。

01/
“‘春山’这个名字是一直伴随我的”
“《春山》是一部耽美小说吗”
如何写作一个可能中国人普遍知道甚至有所了解的王维,对何大草来说不会有很大的困扰——他想写作的,是自己心中的王维。
何大草人生里读到的第一句王维,是“空山不见人”,这句被用在一本反特小说里、作为接头暗号的诗,在当时才10岁的他读来,只觉得恐怖。后来,何大草反复阅读王维,诗集和年谱是其主要的阅读对象。
慢慢地,他就想去王维隐居的辋川看一看,当他从这个以前只能拿来阅读,似乎永远不可能到达的地方归来,他开始写散文、游记,三千字、六千字、九千字,仍觉得有话可说,于是自2017年2月开始动笔,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,写就了小说《春山》的初稿。

辋川访王维,何大草手绘
50、51岁左右时,何大草和一群6、7岁的孩子一起,在一个儿童绘画班学画画,“想把自己打开”。“我的画的色彩是比较浓丽的。我早年的小说的色彩也是比较浓丽的。后来这些色彩都到画里面去了,文字变得更素淡。”

采访当天何大草穿着的T恤上的头像,正是他应学生之请,手绘的作家卡森·麦卡勒斯,这位作家以《心是孤独的猎手》《伤心咖啡馆之歌》等作品,受到广泛关注
YOU成都:为什么叫《春山》?王维写诗,好像多写空山,写秋山?小说为什么叫《春山》?
何大草:王维写山,可能是秋天的山,写淡、写空、写无。“春山”,我开始写的时候就确定了这个名字。我有的小说可能一开始有个名字,到后面就把标题改了,但“春山”是一直伴随我的。我看到这两个字就看到一种生气勃勃,大自然的生命力,是新绿。
但是在这样的春天,作为一个诗人、一个个体的王维,他的生命基本上已经枯萎了,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视觉对照。“春山”同时也是诗人心里的盛唐,那种华美,无限的生机。这就是他内心的盛唐,有过的盛世和好日子,当然这好日子里最重要的还不是大明宫的盛典,不是皇帝恩赐的鱼尾巴,是在这个春山里面、在这个盛世里面,有祖六、有裴迪,也有王维、李白,当然也会有杜甫。
YOU成都:可《春山》反而选择了王维人生的最后阶段?
何大草:我刚说的这一切是大家的共识,但我不会去写一个共识,我要去写个人对他的私见,这是我作为一个小说家(要写的东西)。
他(王维)出现的时候已经很憔悴,在生命的最后一年。他经历了安史之乱,当了伪官,差点被发配又被赦免,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人在这个时候内心世界肯定是很丰富的,回忆也是最多的。年轻人可能没时间去想从前,想的是明天我要做啥。但对老人来说,他会想我从前是怎么过来的。

《春山》,摄影/领唱
YOU成都:裴迪这个人物,是怎么被您提取出来作为一个关键角色的?
何大草:裴迪在王维的生活中是不可替代的。他们长时间地在一起,他给裴迪写了那么深情的诗,包括那首《赠裴迪》,我觉得像是一首情诗。我写了那么多他们之间的对手戏,都是来自王维的一首诗,《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》,在山中,以五柳先生陶渊明自居的王维,看到裴迪喝醉了,在他面前又唱又闹又跳,觉得这种情形是有趣也亲切的,他那么欣赏他。
还有“复值接舆醉,狂歌五柳前”,很多年前我读了这两句,就觉得他们的关系一定是不一样的,裴迪不是王维很多的朋友之一,而是唯一的那个。在王维的人际关系里,他投射出最深情的、唯一的就是裴迪。
YOU成都:这二人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常被讨论的话题?比如我就看到不少评论说,这是一部耽美小说。
何大草:其实我都不晓得啥是“耽美”,我也是看到了这个评价。看到我就去查了一下,之前我对“耽美”啊,“同人”啊这类小说都不了解。我觉得从他的理解来说也是正常的,只是我在写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这个,只觉得两个人的关系很深情、很珍稀,就这样写了。
这种关系,在一个老去的天才,和一个青春的浪子之间,是特别珍贵也很复杂的。这种同性的忘年交,这种情谊是我特别痴迷的。这是一种比发丝还要细的情感的联系,在写作的时候也特别要小心翼翼,可能吹一口气就跑了,带着这种感觉去写,我觉得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。

作家何大草,图源/熊燕
YOU成都:《春山》里还有第三个人物我比较感兴趣,小说里不多的一位女性,一位耳朵受伤的女人。这个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?
何大草:首先有一个历史前提,就是安史之乱中王侯、大户之家纷纷逃难。在古代,战争中最受难的可能就是妇女、儿童和老人,尤其是妇女,胜利者往往以这种方式(伤害她们)来炫耀自己的权力。
我没有正面去写安史之乱的残酷,小说里战争已经结束了,但是它留下了很多破坏,对人的摧残,在这位贵妇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具象的体现。在她身上体现出来的是大唐的坍塌,盛世不在,是王维眼里看到的最直观的东西。
YOU成都:在这里我好像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,我好像看到您关注点上的变化,不再只是文人之间的交游?
何大草:就算对王维这样一位盛世要避、乱世更要避的人,生活在一个很自足的世界的人,他其实也不可能真正做到超脱,孤立于世,他无法生活在时代之外。他的生活随着安史之乱在浮沉,这些是他必须要面对的真相。
他必须要被缺了只胳膊的老兵踢一脚,差点死掉,也一定面对这位被割掉耳朵的贵妇人。他努力想从世界逃脱出去,但我会让他回到这个现场,去面对。
他的人生里一定有这样的时刻,只是他的诗里没写过而已。他不会像杜甫那样去一遍遍写安史之乱。王维会避,“避”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词,避世、避乱、避苦难,但这些实际上他是不可能真正回避的,在某个时刻他一定会惊心动魄地遭遇这些。所以他要么被踢一脚,要么看到这个耳朵残缺的贵妇人。
这两个部分对小说来说是很重要的,如果抽掉这两个部分,那就只是一个孤立地去写王维的生活,和裴迪之间的恩恩怨怨,那这部小说的分量就轻了。

何大草在每一本书上的签名都极为认真

YOU成都:您在写完初稿,到出版之前,我看到有很多次反反复复修改的记录。想知道这个过程中,有没有某处特别记忆深刻的一处呢?
何大草:《春山》18年发表在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上,在小说出版之前,我还是在一些细节的地方做过调整。
这里我印象特别深,有一段讲他(王维)得到宋之问这个别墅,(翻开小说开头和结尾附录处),在出书之前,编辑就跟我商量,说过去散文和小说是分开发表的,时隔有一年多,分开来说无伤大雅,放一起这里就有一些重复,是不是要做一个调整。我觉得这个建议挺好,就把原本简单的叙述,加了一些细节,宋之问在午睡醒来拍死了一只喜蜘蛛,傍晚就被赐死。
这个修改,让宋之问不再是作为一个符号出现的,而是作为一个人走入王维的视野。王维听到这个消息,眼睛里就好像看到了这根细细的蛛丝。虽然当时他才12岁,但好像已经从这根蛛丝这里看到生命的细、脆弱。
YOU成都:这个12岁的少年,您写他眼睛里好像看到了这根蛛丝,放在别人身上可能就不合理。
何大草:是的,你说得很对,王维会,他太敏感了,我觉得他是唐代诗人里最敏感的两三个人之一。有很多隐秘的情感无法表达的天才诗人,一个才几岁就失去了父亲的人,一个长子,又从小跟母亲学佛,他对命运肯定有不一样的感触。
王维看到这根蛛丝,肯定有很多感触,但我没法把他到底怎么想的写出来,只能用这个形象来表达。
这根蛛丝在他眼前飘了又飘,我想可能就飘了一辈子吧。

夜里,为新书签名的作家何大草。摄影/领唱
YOU成都:参加您的新书分享会时,我发现不少的读者,会把《春山》里的王维、李白、杜甫,直接等同于历史上的王维、李白、杜甫。您对此有何看法?
何大草:一个作家不是模拟自然和社会,而是要像一个造物主一样去创造一个世界。过去的细节我们都不知道,我必须用大量的细节去复活它。让辋川的一条河、一棵树都被看到,酒的味道、菌子的味道都能够感受得到,听到他们(王维和裴迪)吵嘴的声音,那这个世界就丰满了。
接下来就是,你写的世界能不能让读者认可,那是取决于你的叙事技巧、你的语言和细节,情节背后的逻辑。一个虚构小说能让人觉得是实有其人、实有其事,他们就按这种方式在说、在想,那我觉得其作为小说来讲,对小说家来说还是会比较欣慰的。至于正确与否,跟小说家来说已经没有关系了。
就像张兆和问沈从文,你写的湘西到底真不真,沈从文反问了一句,你为什么不问我美不美呢?他回避了真假的问题。
这个小说写到这三个人物(李白、杜甫、王维),他们历史上是不是这样都不重要,而是在这个小说里它能不能成立。这三个人,还包括裴迪,他们是不是这样说话,是不是喝的这种酒,他们(王维和裴迪)像夫妻一样斗嘴,如果读者相信他们是这样的,那我觉得很欣慰。
如果他们觉得这就是假的,不可能喝的是汾酒,那我觉得他们可能就从这戏里跑出去了,对我来讲就是我没做好。如果他们读完觉得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,他们就是喝的二十年汾、三十年汾,裴迪就是帮他编文集,王维就是把自己几百封信烧了,觉得这是真的,符合我想象、我理解的王维,这个就是真实的。

织鱼网,何大草手绘
02/
“民族化、文人化、大白话”
“《春山》里的90多个省略号”
1994年的冬天,作家何大草开始写作自己人生的第一部小说:《衣冠似雪》。在这部得名于辛弃疾词的小说里,何大草开始了自己对历史题材小说的大胆探索,即在历史大框架不变的前提下,用小说家的方式写历史,而不是一个故事。
写作26年,何大草写作的题材愈见广阔,也有自己的写作习惯与偏好。在接受我们采访时,他更提到近几年来开始的,在小说语言上的自觉追求与转向。
作家感觉到,自己正处于写作生涯的中场,他希望通过这个阶段的“衰年变法”,能将自己写作时对于民族化、文人化、大白话的追求,贯彻得更为明显——而《春山》,在这个转向里极为关键。
YOU成都:在读王维诗的时候,还会读他的传记或者相关论述吗?
何大草:我读了一些,觉得他们理解的王维和我理解的王维可能不一样。他们可能是通过各种资料、诗文来写一个更社会化、更符合历史真相的王维。我作为作家来讲,可能还是希望写出个人化的王维,有无限多的细节去塑造的王维。
我不愿意把王维的小说写成学术研究的故事版,或者普及版。
我举个例子,我过去写过一部小说,是关于荆轲刺秦的,叫《衣冠似雪》。那是我写的第一篇小说,1994年1月份开始写的,冬天,我也不晓得能不能把它写好,但我对这个故事很熟悉。
我大概十来岁的时候,那时候批林批孔,把古人划分为两个阵营,一个法家一个儒家。法家就是符合社会潮流,儒家是孔老二,拖住社会的车轮不准它往前走的。荆轲就是儒家的小丑,他要杀掉法家(秦王)这个符合历史潮流的大英雄。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故事。
后来,很多历史就要重新来评判,孔夫子就是个伟大的人物,荆轲就成了英雄。再后来到了川大历史系,很认真地阅读了《史记》,《刺客列传》里这段很详细,很精彩,大家都很熟。那是大学的时候,二十来岁。
但当我要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已经三十出头了,我想司马迁已经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版本,那我一定要写得和他不一样。比如说最后宫殿上,《史记》里什么样子可能大家都很清楚,我就想我一定不能那样写,因为那样写了就是一个故事版,它不是一个小说家要做的事情。我就改写了这点,荆轲在秦王面前打开了包裹,拿出一张图,那个匕首出现了,是一把竹剑,是秦王家族传下来的,每天晚上都放在他枕头下的君王之剑。
YOU成都:这样的改写收到了效果吗?
何大草:我写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写法能不能被接受,但我认为小说家应该这样写,荆轲是一个士,他不是一个武士,不是一个工具,所以我心目中荆轲他就做了这样的选择。
小说在《人民文学》1995年发表后,读者评价最高的也是这个改写的部分。它给了我一种鼓励,这以后我写历史小说的时候,在历史大框架不变的情况下,我都是用小说家的方式在写历史。

茶与《春山》,摄影/钟鸣
YOU成都:《春山》其实只有短短几万字的篇幅,而且在写作的时候,您好像还会有意识地不说清楚,欲言又止,像禅宗的机锋。
何大草:我觉得这个就是王维的方式。
王维是有保留的人,“诗禅”这个名号不仅仅是说他写了很多禅诗,也同样是在说他的个性,对人生的理解,他不需要说满。历史上王维学禅,这肯定会影响他说话的方式。我们看到王维的诗,确实最好的那些都不会说得很干净、很透彻,好像就只喜欢开个头,更多的东西在后面。
YOU成都:您也喜欢用省略号,我简单数了数,没数错的话仅仅是王维一人就用了90多个省略号。这也是一种形式上的需要吗?
何大草:过去其实我特别不喜欢用省略号,我也告诫我的学生要慎重(使用省略号)。其实人们用省略号一般会用在一个段落或者文章的最后,但在《春山》里我可能大都使用在中间,这个也算是刻意的。
因为王维这个人,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了,说话吞吞吐吐,可能有些故意的口吃,一句话说了一半可能就故意不想说了。他不畅快、不痛快,有很多言说之难。
YOU成都:您也喜欢用短句。
何大草:对,我喜欢用短句。
可能在早年的时候长句、短句都有,这些年我的写作里好像更喜欢用短句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好像越来越不想在一个句子里带太多的意思。我觉得短句在中国古典文学里,取得了重大的成就,用笔简省、节制,但传达的东西却非常丰富。
写《春山》的时候,我把这些年对小说、对语言的感觉都放在里面。我现在追求的一个目标是,将民族化、文人化、大白话统一起来。
你看《春山》其实没有特别的情节、特别激烈的感情,这是一种文人化趣味,是刻意地在和故事的、龙门阵的语言拉开距离;民族化,就是不走翻译文学的腔调,回到我们自己说话的、写作的古典传统。大白话,是想用生活化的语言。


封面上“春山”二字,是何大草自己写的,目录上的数字序号,是出版社从古人的手迹或字帖里集来的。作家本人很喜欢这本书的装帧制作,“朴素、讲究,又脆弱,很像王维的诗”。摄影/领唱
YOU成都:您说的这种在语言上的追求,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自觉呢?是从《春山》开始的吗?
何大草:我从小在阅读小说时就很重视它的语言。我在一个很匮乏的时代长大,但小时候读了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,就好像有了一种垫底的东西,但同时也树立了一个标准,所以一直就对语言很挑剔。到了写《衣冠似雪》的时候,我就对语言比较重视,但把这三者放在一起,可能是最近。
如果我写小说分成上半场、下半场,那么五十岁以前可能是上半场,五十岁之后算是下半场,或者说中场嘛,(顿)但愿是中场吧。在这个阶段,我可能就有了更多对语言的讲究和自觉。
YOU成都:您说您写作的时间有上半场、中场和下半场这样一个段落的话,您觉得《春山》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序列里边?
何大草:这样举个例子,齐白石到60岁左右的时候,朋友建议他要改变自己(的创作风格)。他在回忆录里面就说是“衰年变法”。我们今天看到的齐白石最伟大的作品,就是“衰年变法”的结果。
我是1962年出生的,对我来讲,可能现在也处于一个“衰年变法”的阶段,那我能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、达到什么样高度的作家,我不敢说,但我觉得我正处在这么个阶段。
这个阶段说起来有点模糊,但也可以有清晰的自我表达。我现在可能要走这样一条路子,就是一开始我觉得我受翻译文学的影响其实都不是特别大,但是也还会有一些,但不自觉地我在拉开这个距离,到了50岁左右的时候,我开始有意识地去拉开。
现在尤其是这样子,在《春山》里面能更清晰看到它的语言的表达方式,它的节奏、内容。我说的民族化、文人化、大白话,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以后的写作可能会贯彻得更明显。
所以可以说《春山》是在这个序列里面很关键的一个,就是在我的“衰年变法”里面是很关键的。
03/
“写作有90%以上是手艺”
“我不是‘学院派作家’”
1999年,何大草开始在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写作课,前年起,他也在屋顶上的樱园开设写作班。在他看来,写作有90%以上是手艺。他主张写作要克制,不能滥情,少议论,要注重白描,写细节,把人物写好……这些在他看来是普遍原则。
教授写作课20余年,学生里有高校的学生,也有社会上的文学爱好者。多年来,他感觉到热爱写作的人,可能永远都是少数,虽然是少数,但,永远都会有。在他看来,文学、艺术就是人类的月光,它可以没有,但有了的话这个世界就更充满了诗意,更像人生活的世界。

何大草在屋顶上的樱园的写作工坊,图源/熊燕
YOU成都:您大学读的历史系,也写了不少历史小说,我想知道这样一种历史的视野,对你的授课也好,对你的写作本身也好,它带来有哪些影响?
何大草:这个问题很好。我觉得一个习惯于去阅读历史的人,你看小说的时候,或者看世界的时候,看任何东西都不是孤立的。
比如王维,他好像是在孤立地生活在他的世界里面,而实际上不是。他的生活一定是被打开了的,一定有一个缺口,和变动着的历史,和那个时代结合在一起。
还有一点就是历史的表述,必须要清晰。在写作上,你可能表达的意味是暧昧的,是复杂的,甚至是一言难尽的,但是在语言的层面上一定要清晰。比如说从终南山上下来,前往长安,他们看到的肯定是长安城的东南角,而不是西北角。
YOU成都:所以你相信写作是可以教学的?
何大草:很多人怀疑写作到底能不能教,我觉得写作有90%以上是手艺。国外很多大学里就开写作学专业,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作家。
打个比方,英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,伊恩·麦克尤恩,就是东英吉利亚大学(文学创作硕士学位)毕业的,他的学弟石黑一雄,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美国还有一个作家,雷蒙德·卡佛,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,回忆他的老师约翰·加德纳上写作课的时候,学生和老师一起讨论一个逗号,讨论为什么是逗号而不是别的什么符号,好像天地之间只有一件大事,就是这个逗号。
YOU成都:您的意思是写作可以拆解成零部件?
何大草:拆解成零部件,然后又如何把它们组合回去。把这些零部件重新组合成一个成完整的工具,一头犁、一台鼓风机、一架马车,这是完全可以训练的,而且绝不可能出现流水线工程,出来都是一样的,为什么呢?因为每个写作者他的个人气质,他的经历,他的家庭,他的血型、基因都不一样。
YOU成都:您开写作课多少年了?长期以来您观察,写作课是更受学生欢迎了,还是热爱写作、想要学习写作的学生在变少?
何大草:在川师是1999年,然后在樱园是前年开始的。我觉得文学永远有人热爱,但真正的热爱是要去写。他通过写和通过画,他的认识的奥妙,那种对美的深度体验才可能达到。这种人永远是少数,过去是少数,现在是少数,但是永远都会有。
文学、艺术就是人类的月光,它可以没得,但有了的话这个世界就更充满了诗意,更像人生活的世界。
YOU成都:您曾经说自己不是“学院派作家”,为什么这么说?您认为“学院派作家”是怎样的?主张您不是学院派,和您认为写作是有技法的,是可以教学的,是不是矛盾的?
何大草:所谓学院,我觉得首先是产生学者的地方,学者是理性的,深刻的。这种理性,它可能比较坚硬,甚至坚硬到有些僵硬,这些东西我作为一个作家要保持距离。
我觉得学院就像各种各样的药品,比如说维生素,维生素b维生素c,它的定量都是明确清楚的,你需要什么就吃什么。但是文学、写作就是水果和蔬菜,它是带着露水的,甚至还带着泥土。虽然它们都是维生素,但是我们经营它的方式和分享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
我在学院虽然21年了,但我有意识地从来不去报一个课题,也不写一篇论文,不报职称,我就是一个在学院生活、在学院教学的一个作家,而不是学者,这是我始终告诫自己的,不能因为在学院我就把自己变成了学者。

山中《春山》,图源/孟蔚红
04/
“就想顺着这条江继续往前走”
“河流不仅仅是河流”
正值生涯中场的何大草,近年来在写作上有更多样的尝试。最近,他的中篇小说《拳》刚刚在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上发表。与《春山》一文一武对称的《拳》,故事背景设于1983年作家大学毕业那一年的成都,是一部以武术之学为核心的小说。
从去年起,何大草开始了全新的写作计划:《顺着水走》。在这部进行中的非虚构作品里,作家计划沿着他家楼下的江安河,一步一步、一段一段地走锦江、岷江、长江,最后走到入海口。他希望通过这样的行走和打量,去了解河流两岸的历史与人。

“顺着水走”手绘路线图,何大草手绘
YOU成都:您最近在进行什么新的写作项目吗?
何大草:我现在开了一个专栏,叫《顺着水走》。我住在温江,家楼下就是江安河,我每天看到河边钓鱼的人,就在想顺着河边走能走多远,我想来试一下,就一步一步顺着水走。水流到锦江,然后在江口流入岷江,在宜宾汇入长江。我就想顺着这条江继续往前走,一直走到入海口。
YOU成都:是打算把这条江走完?
何大草:对,分段分段的,从去年开始,现在大概写了7、8篇。也不是说一口气走完,就一站一站地往下面写。

一个作家和他的老捷达,何大草手绘
在《顺着水走》系列里,作家的代步工具,通常都是一辆老捷达,作家去王维旧居辋川时,开的也是这辆老捷达。这辆车陪伴作家十多年,在他看来,“这车有种笨头笨脑的感觉,吃得苦”,不过因为这车很老了,从去年开始,年检就比较麻烦,于是,老捷达在今年“世界读书日”那天光荣退役。读者们以后可能不太能再见到老捷达,但作家打算“以后如果出本书,我还是会在后记里感谢感谢它”。
YOU成都:您现在走到哪了?
何大草:前段时间因为疫情,走不远,我就写了沱江。沱江边有个小镇叫淮口,在金堂县。
我去找一个同学,他原来就生活在淮口。他回忆说那时候沱江上还是木板桥,没得栏杆,所以每次过桥他都不敢站起来,要爬过去。他回忆起从淮口到金堂县坐船,是木船,早晨六点开船,十点到,每张票是三角五分钱;从那边回来是下水船,三角钱,便宜一点。